那天去同事萧晋家喝酒,晚上太晚了就住下了,
明明家里只有我们2个男人,可是半夜突然发现洗手间里有女人的声音。
深更半夜,酒醉上床,被窝里莫名多了一个女人,这样的事情对于萧晋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,以前每隔十天半个月的总会发生一次,这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愿意用身体换未来的女人。
然而,现在的他可没有睡在星级酒店里,而是穷山僻壤;他也已经不再是那个名扬京城的花花大少,而是一个以“支教”身份躲进大山里的丧家之犬。
为什么还会有女人自荐枕席?更何况,这还是一个非常有韵味和风情的漂亮女人。
俏脸未施粉黛,肌肤在窗外的月光下犹如新剥的蛋清一般白嫩柔滑,仿佛轻轻一戳就会流淌出甜美的汁水一样。
她的眼睛细长,眼角微微上挑,雾蒙蒙的仿佛无时不在诉说着情意,右眼下一颗泪痣,更是为她的双眸平添了浓浓的妩媚。
她的长发黑直如瀑,乌云般散落枕间;她的红唇丰润,微微张着,吐气如兰,不用品尝,光看就知道一定甜过蜜糖。
她的……
这样的极品祸水,要么应该出现在星级酒店的大床上,要么被人用精致的小楼金屋藏娇,可此时此刻,此情此景,却是在穷山僻壤,月光清凉,土坯的房,土坯的炕。
穷山沟里也能养出这么水灵的金丝雀?萧晋不信,说是山精狐怪倒更靠谱一些。
于是,他掐了自己一下,用的力气有点大,很疼。
既然不是春梦,那就得开口问清楚了。
“呃……你是谁?”
套了棉花的被窝很暖和,但女人却似乎很冷,身子一直在微微的颤抖,声音也低的像蚊子哼哼。
“我……我夫家姓梁,我姓周,叫周沛芹。”
自我介绍时先说丈夫,再提自己,这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……不对不对,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,这娘们儿有老公的啊!
卧槽!老子不是遭遇了乡村版的仙人跳吧?!
想到这些,萧晋醉酒后的大脑就清醒了,往后挪了挪。
“我不认识你,也没见过你,所以,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?”他的声音不自觉的严厉了许多。
周沛芹也不知是羞涩还是害怕,身体又缩了缩,额头微微抵着他的胸膛,低声道:“是……是老族长让我来的……”
老族长?萧晋想起傍晚刚到这里时为自己接风的那个老人,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,却因为太荒唐,连他自己都不相信。
这世界上或许会有“用女人来招待贵宾”这种习俗的地方,但它绝对不应该出现在礼仪规范已经出现了几千年的华夏,至少深受儒家思想统治的汉民族中不会有。
如果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,那老族长的用意就绝不是“招待”这么简单。
萧晋嘴角坏坏一笑,大手一捞,就把周沛芹紧紧的搂在怀里。
周沛芹“嘤咛”一声,抬起头慌乱的看了萧晋一眼,眼底有不甘和痛苦一闪而逝,只不过光线不好,他没有看见。
“老族长让你来做什么?你的男人就没有什么意见吗?”萧晋沉声问道。
周沛芹身体颤栗的越发厉害了。
“我、我男人八年前就失踪了……老族长说你从大城市来到我们囚龙村当老师,就是我们全村的大恩人,可不能让你受苦,所以让我来……来伺候你……”
说到这里,她咬着嘴唇颤声哀求道:“我闺女就睡在外间,你待会儿……动静别太大……好么?”
这句话就像是古代演义话本里小娘子哀求相公“怜惜着些”一样,很能激发出男人的禽兽欲!
看着眼前羞涩可人的俏妇,再感受着自己身上的一片柔软,萧晋的下身一阵燥热!
他有些把持不住,立马环住了周沛芹的柳腰……
周沛芹被他这么一搂,嘴里喘着气,发出一声嘤咛。
“萧.......萧老师。”
这三个字仿佛是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,萧晋讪讪的收回了手。
在京城的各种酒店大床上,女人向他提出的要求无非都是些皮包、首饰、鞋子之类的,贪心些的也只是想要成为他萧家的少奶奶而已,即便有会哀求他温柔一些的,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情趣。
因为担心吵醒女儿而求他动静别太大的,这还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遭。
特别是再加上前面“萧老师”这个称呼,心里的那种别扭跟罪恶感,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件非常卑鄙和肮脏的事情一样。
“我不明白,”片刻后,他开口道,“我应该不是第一个来你们村的支教老师,就算你们感恩,吃住上优待一些也就是了,用得着……像你这样吗?”
听他这么问,周沛芹惨然一笑,说:“有什么法子?我们太穷了,只要是出去的人,就没一个回来的,有良心的会把婆娘娃娃接走,没良心的……干脆就直接没了音讯。我们都没什么文化,乡里的学校又太远,孩子们不读书,只能跟着种地放羊,将来长大再出去打工……
老族长说,这样下去,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好日子过,可是,我们这么穷,你们这些娇贵的城里秀才怎么可能留的长远?萧老师,你知道吗?这些年来到我们村里支教的大学生,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两个月以上啊!
村里的学堂已经三年的没有老师了,我们穷,条件差,没办法让你吃好住好,除了不要脸用自己的身子,还有什么?萧老师,我求求你,只要你愿意留下来,让我做什么都可以……”
说到最后,周沛芹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往下淌,烫的萧晋胸膛生疼,脸上也火辣辣的。
囚龙村位于群山之中,距离最近的乡镇隔了两座没有公路的山,去一次需要花大半天的时间,如果要去最近的城市,则需要从镇上再搭四五个小时的小巴车,也就是说,村里人想要进城,清晨四五点出发,傍晚五六点才能到。
糟糕的交通让这里闭塞穷困的似乎早已被外界遗忘。
可是,他们没有自甘贫穷,甚至没有选择逃避,努力的用自己能付出的一切,来换取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而自己呢?惹了麻烦解决不了就远遁千里,躲进这个小山村,从没想过去面对、去承担、或者去改变什么。
家财万贯,锦衣玉食,一掷千金,夜夜风流……这一切的一切都迷住了自己的眼睛,浑浑噩噩的生活了二十多年,自以为顶天立地,却不知道,其实都是在混吃等死而已。
要做人,起码也要有梦想和追求,否则,真的和咸鱼没有什么区别。
周沛芹只是一个穷苦可怜的小寡妇,但此时此刻,萧晋在她面前,却感觉到了自己人格的卑微和低劣。
或许,借着这次躲避追杀,是时候做些什么了。
深吸口气,他直视着周沛芹的眼睛,说:“沛芹姐,你别担心,也不用付出什么,在这里,我可以向你保证:不把村里的孩子们教出来,我就是老死在囚龙村也不会走。不仅如此,我还要让你们摆脱贫穷,让你们都富起来,再也不用为了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尊严!”
男人的自尊心有时候是一个很cao蛋的东西,慷慨激昂的大话一说出来,就不好再对水灵灵的小寡妇下手,所以,来到囚龙村的第一夜,萧晋就好好的体验了一把“禽兽不如”有多难熬。
第二天天一亮,周沛芹在黑暗中鼓起的勇气就消失的无影无踪,脸上的红润就没消退过,连正眼看萧晋一眼都不敢,以至于她十岁的女儿梁小月以为妈妈被这货给欺负了,吃饭时,乌溜溜的大眼珠子一直凶巴巴的盯着他看。
萧晋有些郁闷,也有点诧异,不明白像周沛芹这样性子懦弱的小寡妇是怎么活下来的,要知道,即便是在城市,家里没了顶梁柱的女人都避免不了受欺负,更何况是在闭塞封建的穷山沟?
不过,等他出门在村里转了一圈后,就全明白了。
全村几十户人家,至少三分之二是留守的老人、妇女和儿童,其余的男人也大多老实巴交的,周沛芹一个人拉扯孩子虽然不容易,但在没人“踢寡妇门”的情况下,活下来倒也不难。
村子很小,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土坯的,而且许多都已经破败,唯一看上去鲜亮一点的砖瓦房是这里的祠堂,同时也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。
萧晋跟着“小导游”梁小月来到祠堂前的小操场,因为这里是村子地势最高的地方,所以一低头便能看到整个山村的全貌。
他静静望了这个与外界仿佛差了几个时代的村子许久,再抬起头环顾四周群山,虽然风景美的令人窒息,可一想起被窝里跟小寡妇吹的牛,心里就冰凉一片。
你妹呀!先不说这鬼地方有没有产出,就算山里物产丰富,没有路也运不出去啊!这他娘的怎么可能富的起来?
而要修一条盘踞两座山的公路,哪怕就是平整出来一条能供车辆行驶的土路,所需的费用和人工都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,起码现在的萧晋拿不出来。
囚龙山,囚龙村,这名字还真是绝了,连龙都囚的住,何况人类?
娘的,牛皮吹大了。
烦躁的揉揉头发,他也没了继续欣赏山村风景的兴致,扭头就朝周沛芹家走去。
既然没办法让人家富裕起来,起码老师的职责得做好,回去了解一下村里孩子们的状况,抓紧时间备课吧!
回到家一推门,周沛芹正蹲在压水井旁洗衣服,柔美的背影顿时勾起了萧晋昨晚的“伤心事”,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子解气。
“沛芹姐,洗衣服呐!”
本来是没话找话的招呼一声,没想到周沛芹却像是当小偷被抓了现形,身躯一震,扭头瞅见萧晋,白嫩的小脸瞬间就成了大红布,啪的一声把手里的衣物丢进水里,端起盆子就往屋里跑。
干嘛呀?昨儿晚上可是你钻老子被窝的,至于见到老子就跟看见鬼子进村似的吗?
萧晋很受伤,也觉得总这样挺麻烦的,必须把话说清楚,于是他连忙快走几步,挡在了周沛芹的身前。
“那什么……沛芹姐,你再这样,这里我可就没法儿呆了啊!昨晚上我又没对你做什么,你说你干嘛总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呀?”
原本,周沛芹虽然性格懦弱,但也不是没经历过男女之事的雏儿,孩子都十岁了,还有什么看不开的?之所以早晨起床会不敢正眼看萧晋,那也只是因为对于昨晚自己的主动感到有些害臊而已,这一上午过去,差不多也快没事儿了。
可是,好死不死的,萧晋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,本来昨晚就够丢人的了,要是再让他看见盆子里的东西,那可就真没脸见人了呀!
“萧、萧老师,我……我没事,乡下人没见过世面,您千万别介意。”
萧晋听了差点儿没喷出来,心说这跟见没见过世面有毛关系?张嘴刚要再说点儿什么,忽然发现周沛芹神色不对,微侧着身,将水盆揽在怀里,似乎是在遮挡什么。
视线往盆子里一瞄,他的眼睛立马就瞪圆了!
盆里的水很清,水面上飘着一片大红色的布,随着晃动,布下面还有细细的布条在微微荡漾……阅女无数的萧晋立刻就认出了那是什么。
那竟然是一件抹胸,也就是以前俗称的兜兜。
可想而知,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繁华都市、见识过各种各样情趣内衣的萧晋,在看到这样一件传统的旧式内衣时,内心会产生多大的刺激。
一想到昨晚周沛芹如果是穿的是这玩意儿,他就知道自己肯定把持不住。
周沛芹等了一会儿没听见萧晋说话,一抬头就发现这货正盯着自己的水盆,眼珠子都红了,顿时羞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,矮身就要从旁边绕过去,手臂却冷不丁被抓住了。
干咽口唾沫,萧晋哑着嗓子说:“沛芹姐,你说的话……还算不算数?”
周沛芹被他像是要吃人的目光盯的心砰砰直跳,下巴埋在胸前,蚊呐般的问:“什……什么话?”
萧晋有些急,“就昨晚你说,只要我留下来,你做什么都愿意的那句啊!”
这货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,现在被一件兜兜给勾的精虫上脑,哪里还会要脸?一句话把小寡妇的腿都给问软了。
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,周沛芹认命般的点了点头,表情看不出到底是羞还是苦。
“嘿嘿……”一见人家答应,萧晋就傻笑起来,伸手从盆里捞起那件兜兜,一脸猪哥相的抚摸着,“这衣服真好看,是你做的吗?看这鸳鸯绣的,跟真的一……”
萧晋的声音就像是被突然掐住了脖子一样哑了,眼珠子比刚才瞪的还大,满满的都是震惊和不可思议。
在传统女人的认知中,贴身衣物被人见了,跟自己的身子被人看了没什么区别,昨晚上黑灯瞎火的,周沛芹还能咬咬牙自欺欺人,但现在是大白天,还是在院子里,兜兜被一个大男人拿在手里,羞急的她眼泪都要下来了。
“萧……老师,衣服是湿的,别、别弄脏你的衣裳。”
说着,她就想把兜兜夺回来,可萧晋的手很用力,不但没拿回来,反倒被他一把又握住了手。
“萧老师,你……”
“沛芹姐,这鸳鸯是你绣的?”萧晋瞪着眼睛问。
周沛芹这会儿已经吓坏了,除了点头一个字都不敢说。
萧晋的眼睛亮了起来,声音也抑制不住的激动,“这绣工,你是从哪里学的?”
周沛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,老老实实的答道:“绣法是囚龙村梁氏祖传的,村里的女人基本都会,我也是嫁过来之后学会的。”
“你说什么?村里人都会?真的吗?”萧晋不敢置信的问道,抓住周沛芹的手也不自觉用上了力。
周沛芹吃痛,忍不住道:“萧老师,你……轻点……”
“对不住对不住!”萧晋醒过神来,连忙松开人家,可激动的心情实在无处发泄,双臂一张就将小寡妇给抱了起来,一边转圈一边欢呼道:“哈哈哈……沛芹姐,我知道该怎么让你们富裕起来啦!”
“咣当”一声,周沛芹手一软,盆子掉在了地上,水花四溅。
天绣,取“天衣无缝”之意,起源于宋朝,因为其针脚细密,栩栩如生,就像是工笔画出来的一样,故而得名“天绣”。
不过,古代主流社会追求中庸之道,认为物极必反,凡事都不讲究太“满”,大衍之数中都有一个遁去的一,所以,绣工在“天绣”中,总是会故意留有一点缺憾,以示对“天数”的尊敬。
或者是一片被虫子咬了一口的树叶,也或许是小鸟缺失的一根爪子,总之,就是在完美的技艺中,人为的制造出一点点无伤大雅的不完美。
就像萧晋手里这件兜兜上的鸳鸯,其中一只的喙上只有一个鼻孔,如果不是他曾经在爷爷的一个老友家里见到过“天绣”的收藏,根本就认不出来。
现今,随着科技的进步、外来文明的入侵、信仰的缺失和生活压力的增大,华夏许多传统工艺都已经绝迹或者濒临失传,而“天绣”就属于后者。
据外界统计,迄今还懂得这种绣工的大师,可能已不足五位,而且几乎个个都是花甲之年,一年半载都不一定会有一件作品面世。
现在,周沛芹居然说全村的女人都会,哪怕刨去年纪太大干不了的和年纪太小不愿意学的,剩下正当壮年的妇女也有二三十个呢!
就算她们都还达不到大师级的水平,那也足以让她们过上优渥富足的生活了。
兴奋过后,萧晋放下周沛芹就冲进了屋。周沛芹不明所以,跟进来一看,见他竟然在收拾背包,顿时就吓坏了。
“萧老师,你这是要做啥?”
萧晋头都不回的说:“进城。”
周沛芹脸都白了,呆怔片刻,一咬嘴唇就对身后的女儿梁小月道:“小月乖,你去找二丫玩,吃晌午饭的时候再回来。”
梁小月还不愿意去,周沛芹把眼一瞪,也只好噘着嘴乖乖走了。
等闺女出了院子,周沛芹就把大门闩上,冲进屋抓住萧晋收拾背包的手,带着哭腔哀求道:“萧老师,昨晚是我不对,没有伺候好您,您千万别生气。如果您想的话,现在就可以,想做什么都行。”
说着,便握着萧晋的手朝自己身上拉......
…
未完待续.....
转载自公众号: bzxj29
















-100x100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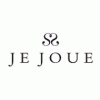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.jpg)